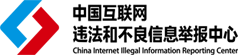纸的味道
□龙治忠
为了去看古法造纸,我们来到丹寨县石桥村。
今年的春天格外多雨,这让流经石桥的小河显得青春而又温情。那长满青苔的水车正咯吱咯吱地转动,两三只水鸟在河面上嬉戏、飞翔。依山傍水的村庄,在水中留下一个朦胧而又曼妙的身影。
丹寨县旅游办的小杨是位热情爽朗的姑娘,她把我们领进了接待中心,简单地介绍了石桥的情况后,就把我们带到村庄西端一个叫穿洞的地方。这是一个天然的溶洞,洞内宽和高各约二三十米,溶洞口水流湍急,溶洞内建有四五间小木房,架着一部水车。房前放有碓与甑,砌有槽和池,手工造纸所用的器具一应俱全,整齐摆放。我们到达穿洞的时候,洞内的水车正转个不停,水流带动木碓高高地举起又重重地落下。在“咚咚”声中,那已被浸得发白的构皮正一点点地被舂烂,渐渐融成纸浆。造纸的师傅刚离开,纸槽还是湿漉漉的,案板上压着一叠薄薄的、软软的构皮纸,渗出的水顺着案板滴进木桶里,叮咚作响。虽然很想探索一下洞的深处,无奈深处没有灯盏,我们只好原路返回。
村里有条叫纸街的短街,有些逼仄,但年代绝对久远。那些铺就街道的石板已经被风雨和脚印磨得光亮如镜,倒映着漫步的牛羊、匆匆的过客以及如水流逝的时光。街边的农舍古朴而低矮,屋檐下的狗儿鸡儿们,正从街的这边晃向那边,一副悠哉的模样。一些妇女坐在门槛上,正忙着削构皮,或者在刚刚抄出来的纸上放上一朵花儿、一片叶子,摆弄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融进一缕缕草木的芳香。男人们呢,有的在浆灰、有的在碓料,也有的在压纸、晒纸,或者揭纸。卖纸,那自然是小姑娘们的事情。她们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嘴甜,正忙着与顾客谈价、选纸、数钱、包装……我们还遇到了一群外国游客,他们也在感受着古法造纸这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虽然我们没有交流,但从他们的笑容里,我读到了他们的兴奋与惊讶。
穿过纸街,我们继续向村庄的深处走去。一路上见到许多露天的煮甑、遍地的浸池,还有随处可见的木榨、纸槽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物件。这些器物的形容,都与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的图谱十分相似。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一壁崖根下,这里有一家比较大的造纸坊,十多个造纸师傅正忙碌着。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架有两根晃悠悠的竹竿,吊着一片密匝匝的竹筛。只见他们两手执着筛沿上的手柄,往纸浆池里一压,然后一摇、一摆、一斜,再一回,随即将网筛提上来,一连串动作熟练顺滑,看得人眼花缭乱。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师傅早已经揭开纸筛,把湿纸堆到案板上了。我们看得有趣,于是从师傅们的手中接过竹筛,学习如何抄纸。一筛,不成,再来一筛,还是不成。看到我们笨手笨脚的样儿,师傅们笑得东倒西歪。可我们没有放弃,缠着他们手把手地教。慢慢地,我们也学得有些模样了。
我忽然意识到,石桥的造纸法是否与蔡伦有些关联呢?请教了一位师傅后得知,确有极深的渊源——即便是现在,石桥的人们在起手造纸的时候,都得先祭蔡伦。师傅还告诉我,石桥人祖祖辈辈都会造纸,如今,村庄里的潘老三和王兴武两人都有绝活,产业也做得最大。他们用古法所造的皮纸销到了东南亚,甚至远销到了欧美。当我们问到谁的造纸技术最具有现代特色时,师傅却说并不是刚才提到的这两位,而是一位从北京来石桥不到三年的韩怀彦老先生。听了这话,我们十分好奇,于是决定去拜访韩先生。
先生和蔼,曾经是报社的记者、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对古法造纸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纸乡石桥,建了几间木屋,还养了几只土鸡,几只小鹅,过着田园诗意的日子。在韩先生家,他与我们谈到了纸的文化,谈到了他对古法造纸的研究和理解,还与我们聊音乐,聊摄影,聊人生的感悟。从与韩先生的交流中,我悟到造纸并非一门单纯的技艺,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交流,一种态度,一种修行。
天色渐晚,我们依依不舍地与韩先生告别。当我们走出村庄,就要翻过山梁的那一刻,我听到在那炊烟袅袅的河谷上,碓声还在不停地回响……这不是一个人的碓声,而是很多人,仿佛是整个村庄的碓声,它和着牛羊归来的蹄声、鸟儿归巢的鸣叫,还有虫子、草木、花朵的声响,汇成了一曲古典而又动人的乐章,那么和谐,那么迷人,混合着香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