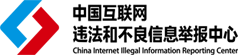1934, 红六军团进凤冈
1934年10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行至石阡甘溪时,突遭湘、桂、黔联军约24个团伏击,红六军团前卫部队仓促应战,与敌激战了近10个小时后,突围冲出甘溪。一部组成先遣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带领下直奔黔东,寻找贺龙、夏曦和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另一部则在红五十一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的带领下也随先遣队向黔东一路而去;还有一些突围时被打散的红军,则在甘溪附近与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由于在甘溪未能击破敌军,军团主力陷入了湘、桂、黔联军的包围之中。在随后近半个月的时间里,红六军团为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消耗。战士们往往是饿着肚子不分昼夜地在北至石阡本庄、龙塘和凤冈天桥、王寨以及思南板桥,南到施秉马溪、紫荆关和镇远路腊、大地方这一崎岖峡谷中辗转鏖战。战斗、饥饿、伤残、疾病使得很多战士掉队,散落在这一带的莽莽大山之中。一直负责前卫开路和后卫断后掩护军团主力南撤转移的红十八师及五十二团的部分指战员约180人分三路于10月16日至18日进入到凤冈境内。
一
1934年10月17日上午,40余名红军顺着本庄至凤冈的山路,走到乌江边大硝洞附近的河闪渡,突遇本庄区长吴登仁派守在渡口处的小股驻军和民团袭击。尽管当时大战后疲惫的红军指战员凭着勇气和智慧,将渡口守敌击溃逃离,并截留住了负责摆渡的船工郑顺和,但也因此伤亡了12人。一直听信反动宣传、害怕红军的郑顺和在红军的说服教育下,用小木船将30多名幸存的红军送过河闪渡,然后又领着他们经麻湾、瓮腰溪、凉风坳,于当天下午抵达天生桥(今天桥镇所在地,当时称天生桥)街头观音洞上的庙子里。那天正值天生桥赶场,郑顺和将红军带到街头观音洞庙里住下后,便借故离开,并在街上将红军来天生桥的消息传了出去。一时间天生桥街上“不得了啦,‘共匪’来啦,快点跑呀!”的叫喊声此起彼伏,那些正在街上赶场的人们也轰的一下就散走了。
红军到达天生桥后分成两路,一部分住在街头观音洞庙里,另一部分则借住在团山堡一户人家的老房子里,并派出一小队红军到街后的关马洞驻扎警戒。红军住下后,通过和当地百姓接触,了解到当地一个乡长陈海阳思想开明、善交朋友、喜做好事,便立即派人找老乡带路去漆树坪乡找陈海阳商议在此借路借住的事宜。平时本来口碑就好,又善交朋友的陈海阳,见前来找他的红军战士说话和气,便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他借故出门,询问了带红军来乡里的老乡,当他了解到红军到天生桥后纪律严明,无骚扰冒犯街上住户的行为后,想到刚才红军已经主动向他表明是借道临时住几天就要走,便进屋答应了红军的请求。
二
据游朝佑老人(当年是乡里的乡丁)生前回忆:“红军应该是在1934年10月18日的那天晚上到达旧寨的,记得那天傍晚我正在漆树坪乡乡长陈海阳的老家旧寨庙湾的屋里,听陈海阳与家人摆谈红军昨天到天生桥后找人与他联系借路借住的事,突然漆树坪乡乡丁队队长丁刚(余庆关兴人)跑进屋来将头附在陈海阳的耳根旁细声叽咕了几句,坐着的陈海阳边听边不住地点头。丁刚说完后,转身便出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几个穿灰色军服的人走进屋来。陈海阳站起身来,与进屋来的人站着摆谈了一小会儿后,便转身安排我和正在屋里的吕瑞清、赵明亮、王树清去打扫他家右边约200米处的庙湾庙子,说是给过江来的红军居住。我们立即拿着扫帚,打着火把去庙里,刚把庙子里的卫生打扫完,约30多名杵棍绑带、互相搀扶的红军,便顺着江边的大路上来住进庙里。陈海阳也带着丁刚从家里过来看了看住下的红军后,便马上吩咐佣人回去背两背篼粮食过来送给庙里的红军,然后他便带着我们上漆树坪去了。”
游朝佑还回忆说他一共给那批红军带了两次路。“第一次是1934年10月19日中午,陈海阳乡长安排我带那些红军去余庆关兴的腊水桥,我将他们带到后便回老家高家岩口了。第二次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高家岩口挖土,突然见一长串穿灰色军服背枪的人,从关兴的腊水桥方向朝这边走来。我丢下手中的锄头,紧张害怕得转身要跑,那些人边朝这边走边操着外地口音大声朝我叫喊道,‘喂,老乡你不用怕,别跑,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自己人,能给我们带路去天生桥吗?我们给你钱。’待他们走近,我一看就是那天陈海阳安排我带去腊水桥的那些人,于是心里便不怎么紧张害怕了,就答应给他们带路。当我带着他们走到漆湾子时,从对面山坡上也走下来一大拨穿灰色军服的人。双方看见后,都立即停了下来,然后互相大声吆喝了几句我听不懂的外地话,坡上的那些人便快步走下坡来,两拨人合在一起。那位叫我带路的人这时也走过来对我说,‘老乡,我们要找的人找到啦,谢谢你啦!’他边说边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递给我,我见才给他们带那么远点路,又想到乡长陈海阳对他们都那么好,便说‘我没给你们带多远,算啦,就别拿带路钱了。’那人却执意要给,我推说一会儿后,他见我执意不收,便将手中的银元收好,又从身上掏出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递给我吃,当时我也确实有些饿了,接过粑粑就开始咬,吃完后我对他们说翻过前面敖溪水山坳,顺着大路直走不远便到天生桥,说完我也转身往回走了。那两拨合在一起的红军也往天生桥方向去了。”
三
1934年10月16日,约40余名被打散的红军来到达平头溪(属凤冈县)对面的上流水口渡口(当时属石阡,现属思南),在当地一王姓船工的帮助下,他们悄悄渡过了平头溪,然后沿塘丝沟、红沙岭、梨树坳顺山路而上,在大塘坳遭遇到提前埋伏在那里的黔军熊加良连和当地保长陈绍武的保丁伏击。顺着大路刚翻上坳口毫无警觉的红军顿时就倒下了一大片,10多个走在后面的红军仓促应战,在密集的枪声中侥幸翻过并逃离大路右边的山坳,翻山越岭地进入茅坝河边的王寨一桶水,并于当晚抵达芭蕉塘。在那住一晚后,第二天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从芭蕉塘转向进入小中山,沿山脊到达与天生桥交汇的四顶山大庙。
他们在庙里休息一晚后,庙里的主持和尚佘大公见红军带着伤员行走十分不便,便主动出面与红军商量,要他们把那4名受伤的红军留下来治疗养伤。红军听了他的建议,同意把伤员留下,并拿了些银元给佘大公。
第二天,佘大公送走那10余名红军后,就立即叫弟子李书银去小河大坡屋基找当地名医陈海大爷上山给红军疗伤。据田井明老人生前回忆:“那段时间我们经常牵牛去四顶山大庙附近放,常看见坡下的医生陈海大爷带着他儿子陈永林上山来给庙里养伤的红军包伤换药。在庙里养伤的红军对我们几个小放牛娃也很热情,教我们唱歌、做木头红缨枪,给我们讲故事。那几个伤员在大庙里休养了一个多星期后,陈海大爷就到小河街上买了4捆灯草,让那4位红军伤员背着灯草,装扮成当地卖灯草的百姓,由他亲自送下四顶山,进梓柏沟往天生桥方向,经茨菇田下河闪渡过乌江去寻找他们的部队去了。”
四
几天后,红六军团主力已东去江口、印江一线,湘、桂、黔联军主力也尾追而去,石阡境内敌人防范相对空虚。在乌江北岸凤冈天生桥一带休整的红五十二团部分红军便离开天生桥,过江去石阡东寻找他们的主力部队。
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部分失散红军过乌江进入凤冈境内后,由于执行严明的革命纪律,让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在这一带群众中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丑化宣传不攻自破,仅几天时间,当地群众就发生了由当初的惧怕红军到认识红军、同情红军,最后到帮助红军的巨大转变。尽管红军在凤冈居住的时间短暂,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给凤冈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红色历史更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凤冈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凤冈县委党史研究室)

今日河闪渡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乌江河闪渡渡口遗址